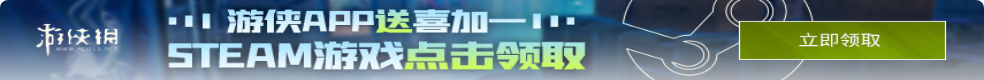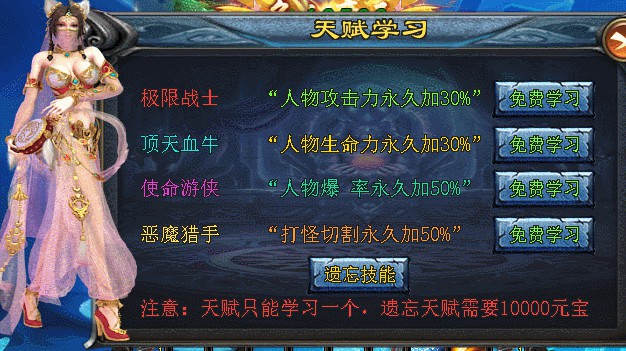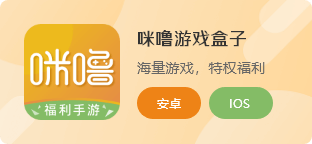晚上8点刚过,治多县西边山包上的垃圾填埋场就“活”了——不是环卫工来收垃圾,是熊来了。

最先出现的是只壮实的公熊,肩膀像驼峰似的凸起,黑耳朵在月光下晃了晃,直接扎进垃圾堆。它双掌刨开沙土,翻出个沾着红油的塑料袋,咬得塑料膜拉丝,跟吃芝士似的;旁边一只母熊带着幼崽,幼崽凑过去舔妈妈爪子上的饭粒,母熊则盯着个色拉油桶,坐地上用腿箍着,嘴往桶里塞,舌头舔得吧唧响。不到半小时,十多只熊陆续来“打卡”,有的啃一次性饭盒,有的叼着塑料瓶,连流浪狗叫都不抬头——这儿的“饭香”比任何警告都管用。

谁能想到,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食肉动物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马熊,如今成了垃圾场的“常客”?

治多县的变化是这一切的起点。十年前,这儿的县中心只有十几间土房,现在成了百余家商铺的步行街:蜜雪冰城的音响循环着藏汉双语广告,幸运咖的咖啡香飘出半条街,快递网点的货架堆得满满当当,外卖员骑着电动车穿街过巷——“以前网购要等一个月,现在三天就到;以前吃糌粑喝油茶,现在顿顿外卖用一次性碗”,23岁的牧民才仁说,现代生活是方便了,可垃圾也跟着“爆发”:快递盒、外卖袋、食品包装,每天装满满6辆压缩车,全拉到山包上的填埋场。

藏马熊的鼻子比狗灵十倍,能闻到几公里外的“饭香”——腐烂的剩饭、辣条的油味、方便面调料包的香气,对它们来说都是“美味”。研究三江源生态的学者周鹏给熊装过定位颈圈,发现现在的熊“变懒了”:以前一天走十几公里找土拨鼠,现在守着垃圾场,活动范围缩到两三公里,“吃垃圾的能量回报是抓土拨鼠的70倍,换你也懒”。更让人担心的是,熊的习性变了——本来是独居动物,现在能凑十几只一起吃垃圾;本来冬天要冬眠,现在零下20度的夜里还来垃圾场“打卡”;本来见了人就跑,现在对着车灯只抬抬头,接着舔包装膜。

才仁的记忆里,熊不是这样的。

小时候听奶奶说,熊是“吉祥的兄弟”,跟人有血缘关系,见了人就跑,连眼神都不敢碰。可他家冬窝子的彩钢房被熊砸烂三次,姐夫每次进门都得先吼一嗓子:“熊哥,我来了!”——怕迎面撞上。才仁的姐夫守着500头牦牛,住在海拔5000米的草山上,他说现在的熊“不怕人了”:“以前见了人撒腿跑,现在站在窗户边看你,跟看邻居似的。”
更让才仁愁的是草场。他家夏牧场的草场上,鼠兔洞密密麻麻,原本没过小腿的草毡变成了贴地皮的硬草——以前熊一天能吃十几只鼠兔,现在见不着熊刨洞了。“熊都去吃垃圾了,谁来管鼠兔?”才仁指着远处的雪山,声音里带着慌:“等风一吹,草全刮走,牦牛吃什么?我们吃什么?”
晚上10点,垃圾场的熊还没走。月光下,母熊带着幼崽扒垃圾,幼崽学着妈样子,用爪子翻塑料袋。不远处的县城里,蜜雪冰城的音响还在响,外卖员的电动车灯划过街头。没人注意到,山包上的熊群里,有一只停下动作,抬头看向县城的方向——它的眼睛里,没有奶奶说的“吉祥”,只有对食物的渴望。
这不是熊的错,也不是人的错。只是当县城的霓虹照进高原,当垃圾场的“饭香”盖过了草山的土味,我们得想想:怎么让熊回到草山,让草场再长出没膝的草,让“吉祥的兄弟”还能做回高原的霸主?
风里飘来垃圾的酸臭味,混着县城的奶茶香。远处的雪山沉默着,像在等一个答案。